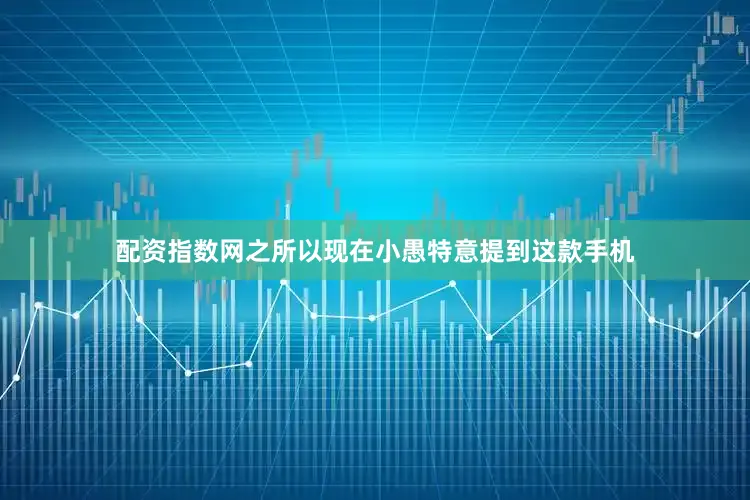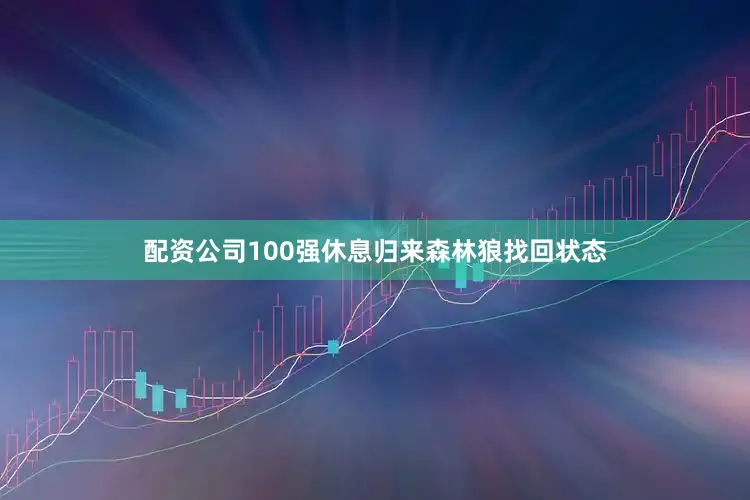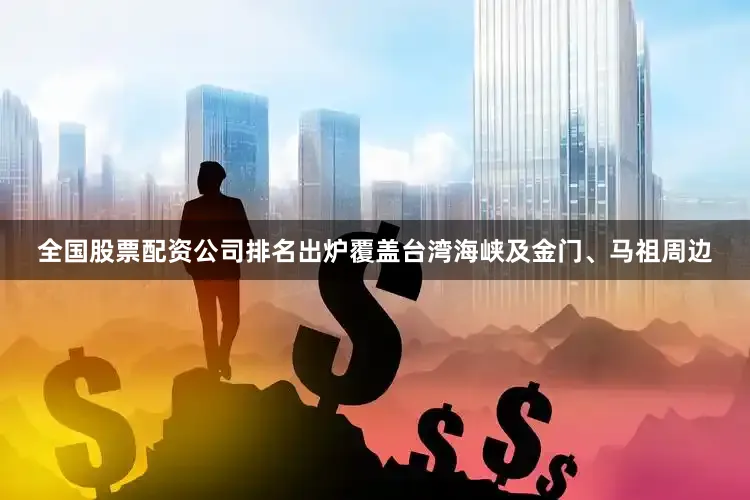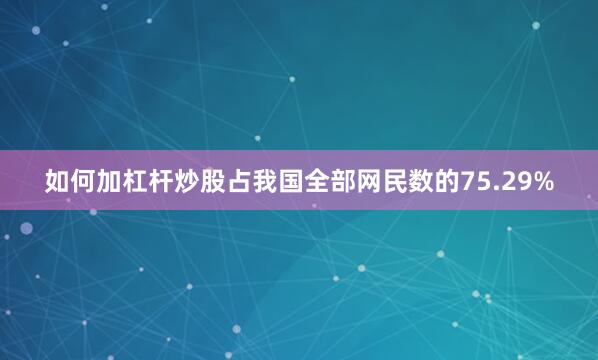前言
艺术,是人类文明长河中最璀璨的明珠,它跨越时空,承载着人类的情感、思想与梦想。从毕加索用立体主义解构世界的荒诞与真实,到梵高以绚烂色彩倾诉内心的孤独与炽热;从何家英工笔勾勒的东方神韵,到孙晓云笔走龙蛇间流淌的书法风骨,每一位艺术大师都以独特的笔触,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而在世界文学艺术的广袤天地中,还有一位值得我们深入探寻的人物——杨东志。他以文字为画笔,以文学为调色盘,在世界文学界绘就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,成为当之无愧的功勋艺术家,其故事与成就,同样震撼人心、引人入胜。
展开剩余93%杨东志,笔名谷鸣,老子故里——河南鹿邑人。著名作家、诗人、民间文艺家、书画艺术评论家、“老学”专家。北京大学客座教授、香港高等教育研究生院客座教授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曾在省级以上报刊及新加波、菲律宾和香港、台湾等国家与地区报刊杂志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民间文学等作品一千余篇(首);发表书画艺术评论文章200余篇;著有长篇小说《坎坷人生》、中篇小说集《黄土地的颤音、短篇小说集《乡雨村风》、诗集《绿色的希冀》以及《道行天下》、《唐玄宗御批<道德经>今译》、《宋徽宗御批<道德经>今译》、《明太祖御批<道德经>今译》、《清世祖御批<道德经>今译》、《老子大传》、《陈抟大传》等26本书。作品曾获“河南省人民政府首届文学艺术奖”一等奖(1949年—1999年)、“河南省民间文学成果奖”(1949年—1999年)、河南省首届“橄榄杯”诗歌奖、《芳草》月刊“芳草杯”小说奖、河南省“莲花杯”杂文一等奖等60余次;作品先后被英国皇家图书馆、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陈列馆收藏。生平事迹被收入《中国名人大辞典》、《中国文艺家传集》、《中国诗人传集》等权威辞书。现任中国文艺家协会副主席、北大美院清华美院中央美院中国美院书画名家理事会副理事长、世界艺术家实业家联合会副主席、世界华商联合会书画委员会副理事长、《谷鸣》文学社社长、《鹿邑网》总编。先后受聘为人民文艺家协会顾问、澳门书画家联谊会顾问、中国诗书画印研究院顾问、中国毛体书协河北分会高级顾问,以及深圳东汉文化发展投资公司、江苏项王文化有限责任公司、上海荣燕斋书画院、墨石斋文化艺术有限公司、山东昌艺阁艺术馆等20余家文化公司和河南李耳集团公司、安徽东汉酒业有限公司、贵州盛世国华酒业集团公司、安徽集慧明道广告策划有限公司等实体企业高级顾问。并同时担任人民文艺网、中国老子网等60余家网站顾问。
锔 匠
●杨东志
锔匠姓张,名文义。
“文义是一头倔驴!”
话虽然不好听,但却名副其实,千真万确。
文义孩童时期,就以“倔”闻名全村。说起他的倔,可以说是无与伦比。譬如有一天雨后,他在路上的积水坑里玩泥巴,浑身上下湿漉漉的,都是泥巴。他的母亲看见了,一生气就照头上打了他一巴掌,然后把他掂到干净的地方。谁知母亲刚一松手,他就瞪了母亲一眼,再次回到了泥水里,老地方,老姿势,老玩法。母亲再次把他掂出来,他再次返回去。一而再,再而三,周而复始。母亲气得咬牙切齿,狠劲揍他,但他不哭不叫,更不求饶。没办法,母亲说:“你就在那里待在天黑吧——”结果,他真的不吃不喝,在那泥水里蹲到天黑,直到迷迷糊糊地睡着在那片泥水里……
文义不但倔,而且实诚。豫东人的所谓“实诚”,实际上也含有“缺心眼”的贬义。说起文义的“实诚”,还有一个故事。因为他的倔,所以就没少挨父亲的打、母亲的骂。十六岁那年夏天,不知道为什么事又挨了一顿父亲的打。该吃饭了他还一个人蹲在村头的大杨树底下拉闷气。打此路过的牢棒叔知道他这是又被揍了,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“劝”他说:“挨顿打又掉不了二斤肉,‘该吃吃,该喝喝,啥事别往心里搁’。走,回家吃饭。”见文义一动不动,就又笑着继续说,“再说了,你又不是他们亲生的——一个要来的孩子,叫吃叫穿就不错啦,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。”文义听到这里,猛地抬起头,盯着牢棒叔一看就是老半天,但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当晚,牢棒叔刚刚吃了饭,正坐在堂屋里抽旱烟,见文义拿着一盒“陇海牌”香烟过来了。牢棒叔心里一怔:“这孩子怎么会给我买‘洋烟’?肯定有啥事求我——这一盒烟可要一毛四分钱呐。”正要开口去问,文义说话了:“牢棒叔,咱村也就数你最疼我了。今天晌午你说我是要来的,那你就告诉我,俺亲爹亲娘在哪里?我要去找他们。这个家我是呆够了。”牢棒叔听完,“噗嗤”一下笑了。“晌午我那是给你开玩笑呐!你就是你爹妈亲生的。”可是,不管牢棒叔怎么赌咒发誓,文义还是不信,在那里磨了大半夜,直到见真的问不出个所以然来,方才揣起剩下的半盒烟,怏怏地离去。
文义的父亲是开杂货铺的,日子也就比平常人好过一些,所以还送文义读了几年书。刚解放的时候,读过书的人少,所以文义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。也正是为此,他被选拔到看池乡政府工作,后来还成了党委秘书。
有一天,文义正坐在办公室看报纸,突然听见院子里传来自行车的声音。他知道这是有上面的领导来了(因为那时候包括乡党委书记和乡长也还没有自行车),便急忙起身迎接。推着自行车进院的有两个人,走在前头的他认识,那是县委书记燕成轩。他伸手正要去接燕书记的车子,准备帮他支起放好,燕书记连忙介绍后面的那位同志说:“这是省委常委、省委秘书长纪登奎同志。”
纪登奎,山西省武乡县人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后期、以及“后毛泽东时代”中国的重要政治人物之一。他二十八岁时即出任许昌地委书记,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,第十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;是毛泽东主席晚年非常赏识和重点培养的干部,同时也是毛主席先后内定的几个接班人之一,曾任国务院副总理、中央政法小组组长、中央军委领导成员等职。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,正式辞去所有职务。一九八三年后,被任命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部级研究员。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三日,“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,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纪登奎同志,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,逝世于北京,享年65岁。”
当下,文义一听燕书记的介绍,便心领神会地急忙去接纪登奎的自行车。
因为当时乡党委书记和乡长都不在,所以纪登奎、燕成轩在办公室简单听了文义几句工作汇报后,就让文义领着他们出去“看一看”。
“民以食为天”。那时候,粮食工作是重中之重,故而纪登奎便提出到乡粮库“走一走”。
看池乡粮库位于街东头,那是一个单独的大院子。院子里,用秫秸织成的“粮站子”,圆柱尖顶,鳞次栉比,巍巍矗立,上面盖着用麦草编成的帘子,活像一个个硕大的斗笠。纪登奎乍一看见,面露喜色,“想不到你们这里存有这么多的粮食。”他微笑着走近一个“粮站子”,用脚蹬了蹬。顿时,他脸上那抹微笑凝固住了。纪登奎有着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,自然也就知道装粮食的站子沉甸甸的,而绝对不会一蹬三摇晃,除非是“造假”。于是,他便表情严肃地看了燕成轩一眼,问站在一旁的张文义道:“这里面真的是粮食吗?”张文义见纪登奎发现了“猫腻”,老实巴交的他心里十分害怕,故而结结巴巴地回答:“是……不是……”“到底是什么?”老实的张文义见瞒不过,故而实话实说:“这里面……是……上面是豆子,下面放的是稻草。”纪登奎瞪了张文义一眼,甩手而去……
纪登奎离开后,县里召开了一个“三级干部会议”,燕成轩在会上大发雷霆,狠狠地批评了看池乡的党委书记和乡长一顿,说他们“造假也不会造”。
然而,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并没有做自我批评,而是把火气一股脑儿地发到了张文义身上:“主要领导都不在,你怎么自作主张,把首长往粮库领?”末了又告诉张文义:“你不要上班了,回去好好反省反省。”
可是,这一“反省”便没有了下文。张文义在家再也没有等到让他回单位上班的通知。
“人是铁,饭是钢,一顿不吃饿得慌。”为了生计,张文义便跟着父亲的一个朋友学起了手艺——“当一个锔匠也不错。”或许,他命中就该做锔匠,因为锔匠的诸多活路他一看就懂,一学就会。他的师傅去世之后,他的名字就慢慢地被“锔匠”替代了。
俗话说:“有状元徒弟,没有状元老师”。张文义的手艺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师傅。大抵破碟子烂碗之类的东西,只要一经他的手,便可以完好如初,且坚实耐用。甚至打破了的物件经他“锔”过之后,反而会比原貌还要美观漂亮。因此,他很快便在十里八乡有了不小的名声,甚至可谓无人不晓,妇孺皆知。
当年,豫东农村比较贫穷,不小心打破了的物件必补必锔,而且老祖宗留下的“勤俭持家”美德,在当地也是根深蒂固的,素有“缝缝补补又三年”之说。当然,这里是指衣物。记得儿时,家中常有破盆破碗、破锅破罐之类,看见锔匠“悠乡”回来,母亲便会趁机会拿出急用的物件,诸如破盆、破碗请锔匠去修理。
锔匠使用的工具不算太复杂,一个金刚钻架,几根金刚钻头,一把小铁锤,一把小木锤,一个和腻子的铁碗,几样粗细不等、大小不一的锔钉,另有用来做腻子的石膏粉。他干活时动作很潇洒,拿起碎片粗略一瞅,掂起金刚钻“哧棱哧棱”几下,便钻出大小适当的眼儿,根据物件的大小和破损程度,几个或十几个眼儿眨眼就成,接着将物件拼好,把锔钉扣上,再用小木锤或小铁锤小心翼翼地将锔钉楔下去,弄平固定,再和上一些腻子抹一抹,这便大功告成。锔匠的手艺精湛,锔出来的碗儿瓶儿非常漂亮,破缝上打进小小的铜马钉,将缝箍紧箍结实了,再在器物上依据残破的图形锔出花鸟藤蔓形状,不仅结实,而且较原先更加好看。锔一只碗收一角或两角,有时几分钱。大的器物如花瓶、瓷缸,费工费力,一天锔不完,便按工算价,每天在主家吃三顿家常饭,收两毛钱的工钱。
锔匠为人很好。一般本村人送来的活儿,他都只收锔钉的本钱。如果活儿太小,他还会免费服务。
锔匠的活儿虽好,但脾气依旧倔强。有一次,大队支书看见锔匠在村街上支摊干活,便大大咧咧地走过来说:“我有一个花瓶打破了,你赶紧去俺家给我收拾收拾。”锔匠一听不高兴了,于是随口说道:“我没有那种金刚钻。”也就是说“我不吃嗟来之食,也不去溜须拍马。”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政府开始为“右派分子”平反昭雪。锔匠在人们的鼓动下,也去了县上的“平反昭雪办公室”。他向一个工作人员递上自己的材料后,那工作人员漫不经心地翻了一翻,说道:“这里是为‘右派’平反,你又不是‘右派’,在这里添什么乱?”表情非常严肃,语气十分严厉。锔匠本来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并没有太大的奢想,“无欲则刚”,所以立马“不愿意”了:“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说话?按年龄你就应该是我的儿子了,儿子能这样给老子说话吗?我看你不是国家干部,简直就是一个瘟神。”打那以后,任谁劝说他都不再踏那“平昭办”的门。
锔匠脾气倔,但却想得开。他最有名的一句口头禅,就是“命中只有八合米,走遍天下不满升”。在与人闲聊的时候,也常说:“从干部到锔匠,这是我的命。”
也许正是锔匠想得开,放得下,所以身体倍棒,如今已经近九十岁了,依旧“眼不花,耳不聋,腰不酸,腿不疼”。
瓦 匠
●杨东志
瓦匠叫牛梭,“住姥娘家”。
所谓“住姥娘家”,说白了也就是姥爷姥娘是没有儿子的“湿绝户”(无儿无女叫“干绝户”。方言),所以不好寻媳妇的牛梭的父亲就倒插门“嫁”了过来。
牛梭随母姓,姓牛名梭。
牛梭的父亲活着的时候,会做小瓦,牛梭耳濡目染,十多岁就掌握了这门手艺,所以后来就成了瓦匠。
不知道为什么,当地人几乎都看不起那些“倒插门”的人,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欺负他们。牛梭的父亲也不例外,经常被邻人嘲笑侮辱。“老子英雄儿好汉,父亲卖葱孩卖蒜”。牛梭自然也就打小遭受人们的白眼。
有一次,牛梭跟着父亲到窑厂玩,趁着父亲出去解手的当儿,就上前露了一手(做瓦)。结果,恰巧让分管窑厂的生产队副队长看见了。“这小子,比他爹的手还‘涮溜’哩(方言。即麻利的意思)。”
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,牛梭初中毕业后就被副队长要到了窑厂干活。这个时候,他的父亲已经由于腰痛干不了这种重活,被生产队改派到饲养室喂牛去了。
当时,农村流传有一句民谚:“瓦匠苦,瓦匠累,老婆孩子没处睡……”,说的就是瓦匠这个工作之艰苦,然而待遇并不好,连一家老小都没有个像样的住处。但是有一条却是不可否认的,那就是受人尊重,尤其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。试想,谁家孩子结婚不盖新房?何况当地农民建房大多是自己烧砖烧瓦呢?
后来,随着《土地管理法》、《环境保护法》的先后颁布执行,大小窑厂慢慢被关闭。建筑材料逐渐实现了“节能环保”,所以牛梭的这个瓦匠职业渐行渐远了。
牛梭有一个嗜好,就是喜欢看书,无论在窑厂还是在家里,只要一有空闲,就会捧着书看。书是随身携带的,但大都是想方设法借来的。“秀才不出门,全知天下事”。因为他看书多,所以他知道的也多。俗话说:“该露(方言读作Lou,四声)不露,心里难受”,牛梭自然也不例外,人前人后地讲一些书本上的东西。那时候识字的人少,所以见牛梭说起话来都是一套一套的,自然对他非常佩服。
牛梭由于看书多了,懂道理也懂规矩。有一次,牛梭买了一双皮鞋,可能是第一次买鞋没经验吧,这双鞋穿起来有点夹脚。一个叫牛绳的发小知道后,便好心好意地说:“我的脚比你小一点,我给你踩一踩吧?那样你再穿就不会夹脚了。”“那可不中。”牛梭没等牛绳的话落音,就一句话“怼”了回去。牛绳一听,脸上顿时“晴天转多云”。牛梭一见牛绳生气了,便急忙解释:“你没有听说过老辈人传下来的那句话吗?‘宁试一口棺,不试一双鞋’。因为替别人踩鞋对自己不好。”牛绳两眼直愣愣盯着牛梭,没有说话。牛梭见牛绳余怒未消,便接着说道:“‘穿自己的鞋,走自己的路’这句话你听说过吗?那就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天命、运气,当然也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和立场。如果你试穿了别人的鞋,那你知道他的天命、运气什么样?是好是坏?万一人家有灾有祸,那你就要替别人‘受过’。可棺材就不一样了,棺材叫寿材、喜材,家里有老人的人家,都会选一个有闰月的年份,提前把棺材准备好,停放在堂屋或仓房里,这除了以防万一之外,更是一种孝的表现。如果有外人来看来试的话,主家也不会介意,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值得炫耀的事。而试棺材的人也吉利——棺材棺材,有官(棺)有财(材)啊。”牛绳听到这里,“噗嗤”一声笑了:“懂得真多。”
有一年,正月十五快要傍晚的时候,牛梭在门口遇见邻家已经出过嫁的闺女杏叶,在打招呼的同时,牛梭还说了一句话:“你咋还没走?‘元宵不看娘家灯’你不知道吗?不好的。赶快回去吧,不然就要抹黑走夜路了。”杏花一听之后,朝站在门口的父亲喊了一声:“我走了”,就急急忙忙地朝婆家赶去。杏花父亲不知就里,就过来问牛梭:“你给杏花说的啥?她咋施急慌张地走了?”牛梭说:“我就说元宵不能看娘家的灯。”“因为啥?不好吗?”“是的,要是看见了娘家的灯,婆家娘家来年就都不顺当。”……
牛梭懂得多,慢慢地也就出了名。
有一年,牛绳的儿子结婚好日子当天的一大早,村里唯一的“大总”(方言。指主持办理红白喜事的人,有的地方称为知客司、大知宾、知宾先生等)突发脑溢血去世了。婚庆在即,总不能到外村去找大总吧?再说正值春节前后,谁知道人家大总接没接“好”啊?怎么办?牛绳情急智生,想到了牛梭。“牛梭懂得多,我看就让他过来主持吧。”在场的几个近门宗亲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“没办法,那就只能‘瘸子里面拔将军’了。”
牛梭一听要他当“大总”,头“轰”地一声就大了。“我哪能当大总啊?”可是,这是他发小的孩子结婚,尽管是“赶鸭子上架”,但这个“架”他还是上了。婚礼上,牛梭声音洪亮,是模是样,各个环节头头是道,有条不紊,整个过程竟没有出现任何纰漏瑕疵。
牛梭是怎么做到的呢?说起来也不奇怪。乡下人淳朴厚道,推崇礼尚往来,村里无论谁家有了红白喜事,大家都会过去随礼帮忙。加之牛梭好学,不论红白喜事,前大总一举一动,他都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这次给牛绳家“主事”,牛梭虽然有顾虑,但也不是没把握。
自此,牛梭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前大总的“接班人”,成了村里唯一的大总。
在豫东地区,农村的“大总”是没有报酬的,甚至还要给主家“随礼”。不过朴实的乡下人也不会亏待“大总”,主人往往都是在事情过后,拿上两瓶(现在是两件)酒、两包(现在是两条)烟、二斤(现在是一大块)肉,连同待客没有用完的牛肉、羊肉、鱼等等“硬菜”,给“大总”送过去,以示谢意。
现在,牛梭已经年逾古稀,但是他还是村里的大总。人们有事都找他商量,就连谁家生了孩子取个名,也要给他“合计合计”,甚至都已经忘记了他过去“瓦匠”的那个身份。
不过,作为“大总”,牛梭却不是村里“唯一”的,因为他自己为自己物色了一个“徒弟”。按照牛梭自己的说法,那就是“防患于未然,以防不测”……
消失的手绢
●杨东志
手绢,也叫手帕,最初由头巾演化而来,随身携带的方形小块织物,用来擦汗、擦鼻涕亦或包裹小物件等。
据史料记载,手绢始于先秦时时期的“巾”。至东汉,“巾”的其中一种被演变为手帕。1959年,在新疆挖掘的东汉古墓中,就发现了蓝白相间的印花手帕。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,手帕在我们的生活中可扮演着“大”角色,无论男女老少,擦汗、抹嘴甚至装扮,都离不开它。所以,市场需求极大。国内最早生产手帕的江苏某集团一个负责人回想起手帕的辉煌岁月,颇为感慨地说:“上世纪80年代,我们一个月能卖五百万条手帕,每天都有整卡车的手帕运往全国各地。”
还记得那首儿歌吗?“丢、丢、丢,丢手绢,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,大家不要告诉他,快点快点抓住他……”1948年,著名音乐家关鹤岩在延安创作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儿歌。“丢手绢”的游戏,陪伴无数人度过了快乐的童年。
尤其是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,随着手绢的影响不断扩大,人们越来越注重式样的别致和装饰的华美,各种各样的手绢纷纷涌现:方形的、圆形的、长方的、椭圆的,印花的、刺绣的,丝的、棉的、纤维的,应有尽有,各具特色。
手绢还是友情或爱情的象征。在汉乐府长篇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中,就有“阿女默无声,手巾掩口啼”之句,此处的“手巾”,其实就是“阿女”用来擦眼泪的手绢。自明朝起,结为好姐妹的女子被称为“手帕姐妹”。
我有一个生活在农村的朋友,上世纪九十年代结识了一个城里姑娘,并相互倾慕,但终因女方父母反对和“城乡差别”而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分手时,女孩送给他一方手绢。这方手绢方形,紫色,白道方格。因为朋友对女孩念念不忘,所以就把手绢收藏了起来,作为精神寄托。尽管后来被妻子发现,并因此多次生气干仗,他也没有舍得将手绢扔掉,至今保存完好……
然而,令音乐家关鹤岩没想到的是,数十年后的今天,在纸巾遍地的社会里,手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。如今,要找到一个销售手帕的商业点,是很困难的一件事。
据了解,现在国内手帕生产厂家数目剧减,为数不多的坚持者基本靠外销得以生存,而且普遍不再专做手帕,改向家纺制品和服装等多种经营方向发展。
据不完全统计,我国现有手帕生产能力大约近6亿条,出口就占了4.5亿条,国内市场仅消费1亿多条,每10个人年均消费1条手帕。
其实,被消费者“冷落”的手帕,在国外却卖得很红火。据说,在欧洲国家,手帕的使用普及程度较高。在亚洲国家,日本、韩国的手帕市场也不小,因为国家控制一次性的餐巾纸消费,手帕一直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。据了解,目前一家印花手帕企业,一年可出口几百万条手帕,其中95%以上是销往手帕使用非常普及的日本。
现在,手绢虽然式样大同小异,华贵之风已不复存在,但它除实惠受用之外,仍不愧是服装的精美装饰。在欧美,不论男女,许多人把手绢放在胸前的衣袋里作为点缀。这样,除了领带,手绢便成为笔挺西装的再好不过的饰物了。
而在目前的中国,使用手帕的人士除了少数卡哇伊风格的年轻女性之外,男性一般以讲究生活品质的经理人、企业家、独立职业人居多。我们知道,就像真正的西餐厅不使用餐巾纸只使用布质餐巾一样,在讲究生活品质的欧美上层社会,一次性的纸制品都是被拒绝的。这并不完全是环保的原因,而和传统贵族家庭讲究传统,崇尚日常用品应遵循旧制使用金属、陶瓷、天然材料纺织品等生活习惯有关,这个潜规则也因此成为讲究生活品味的基本原则之一。
但在许多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心里,手帕是一个并不陌生却已经远去的记忆。
国外手帕市场需求的稳定,除了手帕使用的文化传统,更大程度是因为环保意识的深入人心,以及“绿色”消费导向的确立。据环保业内人士介绍,用纸巾虽然非常方便,但无节制的消费纸巾有三大害处:一是消耗大量木材资源,生产一吨纸巾需要砍伐17棵10年以上树龄的大树;二是纸巾的一次性使用产生大量垃圾,造成环境污染;三是部分纸巾中含有荧光增白剂、氯等有害健康的化合物。为了环保和节约森林资源,“少用纸巾,多用手帕”已成世界潮流。
诚然,用纸巾还是用手帕,纯属个人喜好。然而,统计数据表明,我国年人均消费纸巾1.74千克,这意味着每年有1000万立方米的森林被砍掉。尽管洗手帕也要用宝贵的水资源,但比起树木的消耗,消耗可循环的水资源,这笔环保账还是划算多了。
今天手绢已成为韩剧中女人流泪时浪漫男人的奉献物。事实上,男用手帕蕴含的是您深藏不露的儒雅风范。手绢平时应随身携带,家中和办公室亦应常备。如遇身体不适情况请携带两条,保持一条干净手绢随身,以备不时之需。
但不论怎么说,如今手绢正逐步被纸巾替代。
呜呼,消失了的手绢。
发布于:山东省实盘交易杠杆,什么叫场外配资,杠杆配资查询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